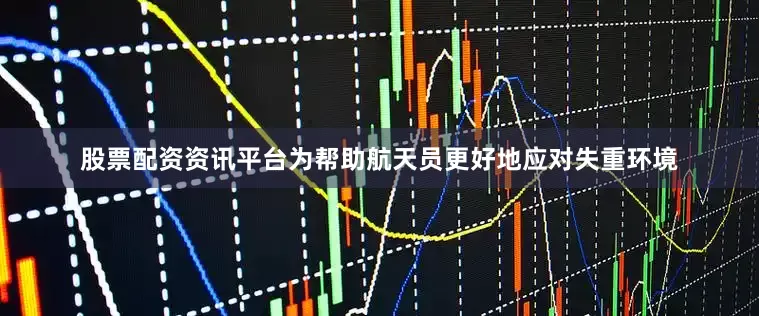
从神舟五号“一人一天”的天地往返,到如今一年两发载人飞船、航天员在空间站“驻留半年”的常态化驻留——在15次载人飞行任务中,李莹辉所在的航天医学全国重点实验室对航天员的健康状况进行了全过程的持续跟踪研究。在轨期间,失重环境会对人体发起哪些生理挑战?科研团队如何构建全周期防护体系?航天员返回地球后,又需经历怎样的“重力重塑”过程?这一连串问号背后,是中国航天医学不断前行的探索轨迹。
城市周刊:航天员进入太空后会有失重反应,尤其在神舟二十号航天员乘组中,有两位第一次进入太空的新同事,他们会有哪些不适?这种不适将要持续多久?会不会对工作产生影响?李莹辉:在太空失重环境下,人体会脱离地心引力束缚,呈现飘浮状态。由于个体体质与前庭功能存在差异,每位航天员对失重的生理反应也不尽相同。部分航天员对失重刺激较为敏感,而另一些则相对耐受。当人体首次进入失重状态时,由于重力消失导致体液重新分布,原本受重力作用向下半身聚集的体液会迅速向头部和上半身转移,同时这一重力变化会引发前庭运动病和空间失定向等症状,通常表现为头晕目眩、恶心呕吐、方向感知障碍等,是航天员进入太空后最早出现的适应性反应。为帮助航天员更好地应对失重环境,航天员在上太空前的准备中会开展针对性的适应训练。当航天员初入太空时,为避免因失重导致的动作失衡,通常会采取轻柔缓慢的动作方式,一边适应太空失重环境,一边与先前驻留的乘组开展全面严谨的工作交接。这些失重反应具有显著的个体差异,部分航天员仅会产生轻微的头晕不适,症状较轻者通过短暂休息即可缓解,如午睡或一夜睡眠后便能恢复。从医学角度来看,这些反应属于正常身体调节过程,是人体适应太空环境的必然现象,不会对航天员身体健康造成任何伤害。

城市周刊:在太空任务执行过程中,航天员王浩泽呈现出较为显著的“浮肿”状况,航天员蔡旭哲好像未出现类似明显症状。这一差异是否是由个体生理特性的不同所导致的呢?李莹辉:事实上,失重反应存在显著的个体差异。正是得益于我国自主培养的航天员队伍和积累的一手数据,我们发现每个人对失重环境的生理响应各不相同;甚至同一航天员身体左右上下的不同部位,在面对失重时的反应也存在差异。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采用“点对点”的精细化方式,逐一攻克相关问题。航天员王浩泽确实存在比较明显的“浮肿”现象,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浮肿,这正是典型的体液头向分布效应。在地球重力环境下,人体约三分之二的体液位于心脏水平面以下。而进入太空失重环境后,失去重力束缚的体液会逐渐向头部转移。这种体液分布的变化并非瞬间完成,而是一个慢潴留的过程。航天员刚进入太空时,这种变化往往并不显著,但随着时间推移,经过一个月左右,这种现象就会逐渐显现。当航天员返回地球后,随着身体经过重力再适应,这些现象将自然消退。城市周刊:神舟十九号乘组返回地球后,目前身体状态如何?他们在返回后需要怎样恢复和重新适应地球环境?李莹辉:目前,神十九乘组的身体状态非常好。在轨期间,他们在高效开展空间站科学实验、完成繁杂站务维护工作的同时,也在按照既定的失重防护方案进行各种锻炼。从太空失重环境回到地球后,首先需要进行重力适应。所以,在返回地球前和刚回来后,要适当补充一部分体液,让航天员的身体状态能够尽快恢复;另外,通过各种动作训练,让航天员能尽快找到脚踏实地的感觉,而不是飘浮在太空中,这需要航天员的神经系统建立起“回到地球”的环路,更好地适应地球环境。当然,这个适应的速度很快。城市周刊:随着中国载人登月工程稳步推进、各项筹备工作如火如荼开展,执行登月任务的航天员肩负着前所未有的使命与挑战。相较于空间站任务,登月对航天员的身体素质、生理机能等方面提出了哪些更高的要求?李莹辉:相较于空间站的失重环境,月球表面呈现出独特的低重力特性,这使得载人登月任务对航天员提出了截然不同的挑战。在空间站中,航天员习惯了无重力飘浮的活动方式;而在月球表面,航天员必须在仅为地球六分之一的重力条件下,重新建立重心姿态稳定控制体系。回顾阿波罗登月任务,航天员也常因不适应低重力环境而意外跌倒。这一现象充分说明,低重力环境下的运动稳定性控制已成为载人登月任务的难点。对于未来执行登月任务的航天员而言,如何在低重力环境中保持身体平衡、精准控制姿态,将是失重防护的重中之重。
用热爱书写星辰答卷
1996年,我踏入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投身于航天员的健康防护和利用空间环境条件下研究人对空间环境的适应。换句话说,我的工作核心就是预判航天员在轨飞行期间身体可能遭遇的失重带来的影响,精准捕捉其身体机能的各种变化,并研究制定科学有效的防护策略。
 李莹辉 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研究员,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航天员系统副总设计师,航天医学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
李莹辉 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研究员,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航天员系统副总设计师,航天医学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
在载人航天事业的发展进程中,航天对科技的牵引和驱动愈发显著。载人航天任务往往会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那些在地面环境中未曾出现的特殊难题,在太空中却会带来一系列的技术问题。以跑步这一看似简单的日常动作为例,航天员需要在太空失重条件下实现发力的精准控制与均匀分布。在地球上,人体206块骨头与639块肌肉能够自然协调配合,形成连贯流畅的动作;而在太空,由于缺乏重力牵引,航天员的运动呈现出“触一点动一点”的特性,无法实现在地球上那样的“触一点动一片”的有机耦合。这一特殊现象,要求科研团队在航天员健康保障技术上,点对点地做到精准到每一块肌肉,确保航天员在返回地球后,身体机能仍能保持协调健康。在攻克太空难题的过程中,将进一步催生智能化、自动化技术的创新需求,以及对人体生理机制的更深层次研究。随着我国载人航天任务在轨时间不断延长,科研团队对这些技术难题的认知也在持续深化,每一次探索都为后续任务积累了宝贵经验,推动着航天医学技术迈向新的高度。

航天作为一个极具特殊性的科研平台,其与地面截然不同的环境,为医学和生命科学研究打开了全新的视角。在太空中,我们得以更好地理解和解读生命在不同环境下的适应特征。参与航天任务的航天员均经过严苛筛选,属于极为健康的群体,但即便如此,进入失重环境后,他们仍会面临一系列医学挑战,诸如骨密度流失、肌肉萎缩等问题。对这些航天员特有的医学现象进行深入研究与解读,不仅有助于保障航天员的健康,更为探索大众疾病的发生发展规律提供了宝贵的启示与借鉴。因此,航天事业一方面要持续优化保障体系,助力航天员实现更健康、更持久的太空飞行;另一方面,需将航天领域积累的理论成果、先进技术与创新方法,回馈于大众健康领域,推动医学进步与全民健康事业发展。
炒股配资时间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